打工文学的真实样貌——读欧阳杏蓬《南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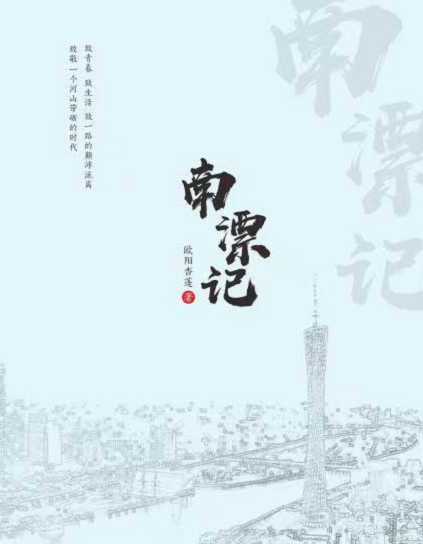
欧阳杏蓬的打工散文集《南漂记》即将出版。
这是一部书写打工生活的散文集,20万字。
欧阳杏蓬,民间写作者,曾任《大周末》杂志主编、《电影评介》杂志主编, 作品散见于《文艺报》《读者》《散文世界》《莽原》《视野》《青年文学家》《作品》《中国文化报》《南国早报》《新快报》《永州日报》《现代青年》《中华散文》等报刊,作品入选多个选本,多篇散文作品被全国各地中学选为语文测试阅读题,已出版散文集《以孤独的名义》(敦煌文艺出版社)、《缤纷湘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个寄居者的广州读本》(云南人民出版社)、《一生两半》(中国文联出版社)、《现实之境》(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我们东干脚》(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等六种。
读过欧阳杏蓬的打工散文集《一个寄居者的广州读本》《一生两半》,文笔温润,真情实感。读《南漂记》,我是越读越沉重,但就是放不下。放不下人在他乡打工的艰难,放不下人在他乡的迷茫,放不下底层的打工者,也放不下打工人因农村变化发生的嬗变。打工是生活选择,但生活沉重,农民工更不易,我是知道的。
我就是要看看欧阳杏蓬是怎样书写打工人、打工生活和人在他乡的离奇遭遇。真就看到了打工文学作品的另一种文本。之前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粗糙劣质的,打工文学不缺小说,也不缺诗歌,但一向缺乏代表性作品,所以,这么多年,文坛并没有重视打工类的文学作品。
《南漂记》是一个突破,是一个扭转。它是中国第一部书写打工人离家、求职、漂泊、探索、在城市生活的全景式的散文集。欧阳杏蓬拿出这样一部接近纪实的散文集,不仅写打工求职的艰难,而且写打工生活的快乐,不仅写进城后的迷茫,而且写打工生活的发展演变和走向,证明打工不仅是农民的突围,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他乡和家乡是打工人生活的两只铅坠。
《南漂记》揭示了一个主题:打工人最终必然走向城市。
那么,写作这样一部纪实性的散文集,不置身于打工生活,是难以发掘和书写的。仅仅是打工作者,不一定写得出来,因为可能缺乏文学的表达;仅仅是专注于一个工种的打工者,也不一定写得出来,因为可能缺乏对南方的整体了解。这个意义上说,是打工生活和文学创作功底的融合,成就了《南漂记》这部纪实性的打工散文作品。这也就是欧阳杏蓬的意义。欧阳杏蓬在南方打工30年,做过很多种工作,从体力到智力,从潮汕地区到珠三角,他太熟悉打工生活,也太熟悉打工人成长历程了。就像他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讲给真正在他乡讨生活的人听的。
作为打工写作人,写工作环境,写他乡生活,他没有将笔触囿限于乡愁乡思,也跳出了生活的艰苦,而是在通过自己的打工足迹向时代辐射,深挖社会意义上的打工潮流,即社会的开放掀起了打工潮,人群求变是打工的源泉力量,珠三角的发展则是给土地上的农民解除了原始束缚。当打工人的欲望以脱离土地束缚,从谋求美好生活伸向身份归属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人的认识改变。在波澜壮阔的打工潮里,这种需求变化不是悄然无声的。那些为改变身份的打工者,不仅努力劳动,而且追求进步;那些已经改变身份的打工者,面对新的生活,疑问打工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打工者比任何一个职业所接触、涉及的生活领域都要宽广。《南漂记》呈现了一个打工者打工所接触的各种工种,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很有地域色彩。这样,作品触及打工生活的一个实质问题:一个努力上进的打工者在自生自灭的生活中如何保持积极上进的精神面貌,这是从复杂多变的生活走向文明社会的根本。
《南漂记》第一辑写了我离开家乡后的打工,作品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然后进入一个过程:“底层劳动者—嬗变—城市精英”。我以为,打工文学如果局限于在打工生活层面书写,可能就是一个社会故事;拓展到底层写工作历程,就进入一种时代故事;而深入到南方各地和各种人物书写,就伸展到社会故事里了。欧阳杏蓬以真实的经历、温和的文字、不同的城市、一样的心态、独特的记述,展示农民——打工——精英的变化演进,显出一个打工文学作者的生活阅历和独到视角。
打工仔这个称谓正在淡出历史视野,打工经历打工生活却被几代人铭记。《南漂记》,书写打工,又超越打工。它揭示的是打工人的生活最终走向:无愧于心的生活。打工潮是中国时代的一个缩影,打工是中国数亿人的出路,打工人影响了世界。
没有《南漂记》,打工散文在打工文学就是一个空白。
《南漂记》无疑是打工文学的一个独特样貌,只属于欧阳杏蓬。(景生)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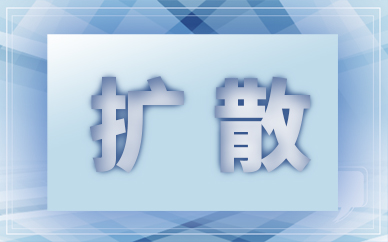





 QQ接收不到离线文件是什么原因?QQ接收不到离线文件怎么解决?
QQ接收不到离线文件是什么原因?QQ接收不到离线文件怎么解决?
 ps3游戏机多少钱一台?ps3游戏怎么安装到外置硬盘?
ps3游戏机多少钱一台?ps3游戏怎么安装到外置硬盘?
 微信怎样设置来自iPhone6客户端?微信怎样设置零钱支付优先?
微信怎样设置来自iPhone6客户端?微信怎样设置零钱支付优先?